我(指乔邦义,以下同)是1937年参加抗日联军的。
我参军时就到了六师。下面就谈一谈我参军的经过吧。
我家原来非常贫困,真是吃这顿没有那顿。这样,就靠借高利贷来维持生活,可是,借了又还不起,生活更加困难。后来,由我父亲白手起家,在吉林省长白县郊区开荒,买了点房子和地。不久军伐张作霖的部队开到我们县一个旅,在我们家那里随便的盖房子,因此我们家的土地也就被他们侵占去了,光给我们剩下来三间小房,给了不几个钱,也就都给他们啦。这样,我家就搬到长白县十九道沟双山头地方,这时我们家已有兄妹七个,我们兄弟五人,还有两个妹妹,我那时已有十四、五岁。我和大哥能干活,每天能挣一块来钱,要是弄不好,就只能挣四、五角钱。碰到没有活的时候,家里的供应就成了问题。能干活的时间是从阳历的九月开始,到十月就完了,要是再去掉下雨阴天,就更完了,所以到冬天就都瞪眼了。想要借钱,向谁去借!虽然是吃那些配给的橡子面,但没钱还是买不来的。那时光听人家说红军,但不知什么是红军,老百姓只听说有个姓毛的和姓朱的红军的头,虽然常中人家讲红军,但总也没看见红军啥样,有人说红军光吃牛、吃马、不吃饭。
到1936年冬天,就见到红军啦。冬天的时候,地方等有钱的人家就回县城去了。在一天晚上红军来到了我们家,问我们要点吃的东西,他们的态度非常好,同时也非常热情,有时还求我们给他们送粮食。当时心里想,这支部队算是啥样的部队呢?有朝鲜人,有老年人,有妇女还有小孩,是红军吗?还不穿红衣服。给他们送粮食以后,他们还专有人给我们讲日本怎样侵占咱们国土;张作霖怎样的不抵抗。这样一来二去就和他们搞熟悉了,他们就号召青年参军。
这时小日本一看红军经常来,就告诉我们说:“红军啥时来就得当即到二十道沟去报告,不报告就把你们统统杀掉”。于是,屯中的坏蛋,在红军来时,他们经常去报告。
红军一来到我们屯,就到我们家,有时求我们买粮,买胶鞋和药品。屯中有个特务,把红军来了的情况报告了日本人。这样,在红军下一次来的时候,就将屯子的房子都烧了,那时同我们在一块干活的有个田尚林,他的房子是秋天盖的,没有全烧,剩下半截,他家里有个瘫痪的老头,在这个老头死去以后,田尚林将家搬到他的岳父家去住了。这样,我家就搬到田尚林家剩下的那半截房子里住。这时,我们对红军有些不满,但红军以后还是常来,那时我父亲患血管崩裂造成瘫痪症,他们来时还给我父亲拿点药,并说明我军是救国的队伍,也说我们都是好人,其它人里有坏蛋,红军来几次报告几次,解释说,要不烧我家的房子光烧别人家的房子,敌人一定要说我家是红军住在“三股青”(即三个山头)地方,胡匪忌讳这地方,他们不愿意去。这时敌人采取归部落,把人家集中,并说,谁要是不搬走的话,就把人关在屋里,连房子带人一同烧掉。这样,把十九道沟这地方弄的鸡飞狗跳墙,当他们烧杀之势距我家还有三、四里路时,我父亲告诉我们快去找红军吧!
那时我与红军已经有联系,当我们哥几个要走的时候,有个害了我全家的特务高相林来了他不让我们走。并说,要走还是往屯堡走别把你们父亲丢了。我们说我们不走。高相林又问我们:“敌人来了你们上那去”?我说上山去住,把他就应付走了。他走后,我们和父亲在一起痛哭一场,然后分别了,这时我联络了不少人,有姓胡的哥三个,还有……。这时高相林并没有走,而是躲起来了,当我们走到一个山坡上的时候,高相林出来了,他说,你们还不要你们的父亲了吗?后来我们痛斥了这个特务,他也就吓跑了。
当天,我们就和抗联一个副官接上了关系。这位副官姓朴,接头的地点是在长白县十九道沟双岔地方,距我家有10里左右,那正是1937年4月左右。
找到朴副官以后,他很欢迎我们,特别欢迎我们哥五个参军。另外有个姓田的还带来了他的爱人,朴副官说不要女同志,因不知啥时生孩子,走路不方便。这样,姓田的夫妇就都回去了。我哥哥因腿有病,加上家里还有一个有病的父亲,也动员回去照顾我们的父亲去了。
大哥回去时,我们告诉他,白天待在山上,等敌人一来你就跑,我们和大哥就是这样的分开了,以后总也没有见过面。
第二天,朴副官领我们就走了,一走走了两三天,过了黑瞎子沟到十三、四道沟那块,我们找到了大部队,我们哥几个就分开了。我分在六师八团三连一排。六师下边没有营,有三个团,实际是两个团,即七团、八团。我在八团三连,连长姓田,是个从老军阀部队跑过来的。那时在队伍里不知谁是党员。一个连有三个排,一个排有两三个班或四个班,连部有个文书,文书兼教字(文化教员),另外还有三、四个宣传员,那时把文书叫字匠,把宣传员叫鼓动员。
团有三个连,团部有个机枪班,有个通讯连,通讯连包括警卫班,送信的,副官处,司号班,司务长,连部下有三个排,有司号员。有四个排的连就要有通讯班,我们那个排就有三个班。
那时只听说有军,不知道军在那,杨司令和魏政委我们都看见过。
我们哥四个就这样来到了部队,但在我们走后,我的妹夫就被敌人抓去了,敌人给他上电刑,他死去了,大哥白天在山上待着。这时,我母亲的一个干儿子名叫刘德恒,他把妹妹领到我家要把我父亲拉去,这时由于妹妹的死,已把妹妹气疯了。于是刘德恒把我父亲拉到长白县的花子房去了,到那里以后,他啥也吃不着。再加上他想我们,已经想疯了,成天叫着乔邦信的小名“小五子啊!”后来,我妹妹把我爹弄她家的马棚里去住去了,这时也总想要跑,不到一年他就死去了。
我的大哥,后来又找到了抗日联军,那时我四兄弟在师部当机枪射手,我们哥几个他是最先入党的。我大哥给部队做通讯工作,冬天不能走,就住在黑瞎子沟掌的密营里,大部队给他们弄了些粮食,让他们接定量吃,这样可以吃到来年春天,他们一共6个人,其中有5个是朝族,他们那时非常困难,有米,有土豆,但是没盐,实在是难吃。这时敌人又出来大“讨伐”,在密营里,有一个人提议要弄点油盐好过年,大家没同意。于是,这个人就跑了,所以便决定要走。当时走是很困难,真是走也得死,不走也得死。第二天早晨,天刚放亮,敌人就来了,打死了三个,抓去了两个,其中就有我大哥一个,这件事是在第二年春天,师长把我找去安慰一番,说我哥哥是英雄。我哥哥被捕后,他改了名换了姓,不然,我妹妹又得受害,这时有个坏家伙说我哥姓乔,我哥哥说他姓孙,不姓乔。小日本的各种刑法他都换过了。师长曾说过我大哥死的很刚强,当用刀要砍脖时,把汽车开到路过我妹妹家门口,把我妹妹提出来,叫他认我哥哥。我大哥怕牵连她家,就甩开我妹妹,说我根本就不认识她,她要给我当小老婆子还可以,就这样把敌人朦过去了。但他们还叫我妹妹去陪绑,这次一共杀了二十几个,我哥哥是第二个被杀的,杀完之后,把我妹妹也就解下了场。
这个时候,我正在八团三连一排一班。
那年冬天雪很深,我向上级要求让我五弟(乔邦信)跟着我,好便于照顾他。
我们参加部队是艰苦的。八团团长孙学峰(可能也叫孙长祥)是个山东人,他始终没有离开东北。1945年8月,在磐石由于我们自己军队发生误会,发生武装冲突而牺牲),那时团长要把乔邦信留在团部。这时三连的连长是田割牙子,他是从军阀部队里哗变出来的,现在看来,他就是一个瓦解部队的叛徒,全连有双好胶皮鞋,好东西都得给他,否则他就要找你小脚,这个家伙一冬天就穿了十来条棉裤。这个人在1938年冬死了。
那时我有胃病,老五又小,姓田的那连长对我俩很坏,但我们那个班的班长,他是共产党员,对我很好。
到秋天的时候,各连就分开活动,到田地里去弄粮食,给养的问题也就不太大了。
到1937年和1938年的时候,抗联二军六师能有一千来人(乔邦信说能有五、六百人),秋天时各连就分开活动。有一次在分开活动时,连长田豁牙子想要把我弄死,说我不是来革命的,是来队内打听情况的奸细。但是,他要枪毙我的主张,没有得到大家的同意,说需要请示团部批准。
那时同志之间的友情是很深的,那怕是有手指头那么大的一点东西,也要分给每个人都吃到点,就是弄到一把炒面,也要大家共同来吃。
我俩参军以后,参加过数次战斗,有些都记不清了。
我曾参加打过濛江,在那得了一些东西,部队指示,可以把富裕人家的东西少拿点,我在一个新结婚的夫妇家里,经他俩同意,拿了一条新棉被,那时田豁牙子连长还活着,他就向我要,我没给他。因此,他又要枪毙我,但是,文书不同意,这样,他也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魏政委率领我们打辉南的那次战斗,我俩也参加了。
这是在1938年的秋天,我们八团和独立旅担任主攻。那时我们团长姓钱,外号叫钱大包,他是山西人,是个共产党员,他就是在这次打辉南后撤出来走20里的地方而牺牲了。独立旅由旅长率领(方振声,也叫方振、方强),这个人以后的情况就不太清楚了。打辉南的这次战斗,在计划上是有些缺点的。敌人在辉南的汽车很多,又加之交通便利,我们在接到攻打辉南的通知时,对到辉南的距离没有摸准确。我们了解城里是一个营的步兵,但敌人是机枪营。由于距离没摸准,所以跑了一宿,是七团一个连找来个老百姓给我们拉道。跑到一个铁丝网前,过不去了,这时小鸡也就叫了,我们那个连就先过了这“铁吉子”,打开了大门,这样里边就打响了。然后外边也就打起来了,这次是我们了解错了,结果没打了,主要任务是往外背布。打了一阵没有打进去,牺牲了不少人,这时天也快亮了。我告诉我五弟说:“你哪也别去(那时他在团部),你到点心铺去弄点点心。他弄到以后,被大家分吃了。在天快亮的时候,来了个通讯员,让快点撤退。领导上让抢一个山头,这时敌人跑到了山底下,我们抢到了山头,敌人也抢到了山头,这样,两下一接触,便展开了一场肉搏战。日本人不多,多数是伪军,我们就喊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伪军一听口号,就不打了,这样把日本人消灭了,这次我们牺牲有几十人,敌人死有几百。敌人从山那边打来的子弹(到这块已没力量了而成弧形)打中了钱团长的胸部,他就这样的牺牲了,他的尸体被我们炼了。这时我们的任务是狙击敌人,七团占了那个大山头,敌人用汽车顺着山沟拉来了正规军,集中兵力包围咱们,这时,师长布置我们团在那阻击,后来又叫一连回来,去援助七团。仗打的非常激烈,这时敌人用一批打仗,一批换下来去吃饭,我们就乘机来个反冲锋,敌人受不住了,开来了几百台汽车沿着盘山道往山上走,我们认死也不肯让敌人把山头占领,我们就先打死汽车司机,然后汽车就往山下滚下去了,打到天黑,敌人也熊了,这时师长下令后退,退到一个萝卜地里见到了师部,那时正是拔大葱的时候。快要上冻了,也就是旧历九月左右,我们从那里下了一个沟又上了一个山,在那森林里就宿营了。那次背的布是相当之多,我们把布藏起来,准备明天和敌人干。那次战斗以后, 接连又打了一个星期,一天最多曾经打过24次仗,但这时我们完全主动了。
打完辉南之后,就到了长白县,这时小日本正搞归屯并户,小屯归大屯,大屯归部落。这可真把老百姓弄苦了。
在一个部落里,起码要有敌人正规军一个营的兵力在那驻防。我们奔长白县打了两个部落,弄了些粮食,然后是成天的跑,成天的打,雪又非常深,敌人又在后面跟着,但他们又不敢靠近我们,怕被我们打死。这样小日本每天用六块钱的价格买兵走在前面。我们顺哪条沟走,他们也顺哪条沟走,有时我们转回身射击一阵,就把敌人打死二、三十人,敌人把前面都放上中国人,他们走在后边,于是我们又专打后边,以后日本人走在中间,我们就往中间打,专打日本人。最初我们抓住日本俘虏也是释放,但有些释放后,他回去尽作反动宣传,所以以后抓住日本人就杀掉。
下边再介绍一个战斗,那就是六棵松战斗的情况。
打六棵松是1938年冬天过年时,我们也是没有侦察好,敌人的布置是这样的,有一栋房子,放一营兵力,但这栋房子屋里挖有一个地洞子,通往山后的一个地堡,地洞子又能往外打枪。
那时我们团包打一个炮台,七团负责包围这个营。这里是小日本在东北一个最大的木场之一。这时我的身体挺好,当机枪射手。机枪班要比别人多背一、二百粒子弹,不背粮食。我使用的是“母暴子”机枪。这是我们第六师的宝贝。开始进攻时团部在我们后边,那时一往前去就有动静,连长告诉一点响动也不要有,每人身上披着白布,这样敌人不好发觉。我们穿过干禾棵子后,进去了三、四个人问说谁?我们也没动弹。敌人还放了两枪。这时它的大门口被七团守了。我们进屋一看没人。这时敌人通过地洞子跑到后山炮台上去了,不一会敌人就动手了,我们却还没看到敌人,所以是单方面打枪。于是师部下令后退,这时连长被打倒了,一看才知道从雪地上打过来的枪(从地道两边往外打的枪)。这时,我们已经有五、六个人被打倒了。我扯着连长的皮带把他救出来,七团还在里边打呢。这次七团损失很大,团长以下30多人牺牲,八团部这时还在道边上。在钱团长牺牲后,团长叫孙学峰(可能也叫孙长祥),团长叫我跟他走,并把机枪架起来向敌人和牲口圈打枪,打死不少敌人牛马,并且还赶出些牛来(几百头牛)。
打完六棵松不久,敌人就跟上来。正在吃饭时,我们连四班长先发现了,他叫逢克巴(有口吃病),刚一说话还没说出来时,从他的下巴打进了一颗子弹。乔邦信这次也负了伤(右手),是孙团长把他救出来的。
八团团部准备赶一部分牛,把敌人引出去,使敌人不撵我们了。后来,我们跑到一个地方,那里有土豆子、大萝卜,我们就在那猫了一冬。
下面我就根据你们提纲中的问题谈几点;
二军六师参谋长林水山是在1939年5月叛变的,他叛变之后,就来了个姓郑的做政治部主任,后来又来了个姓李的。姓郑的在这只有半年的时间。
我四弟乔邦智,他是我们兄弟最早入党的。有一次,去十七、八个人跟师长到军部开会,回来时遇敌,乔邦智负伤,他不能走了。这时有个叛徒告密说里边有个金××,邦智一看要抓金××,于是他就站起来说:“我就是金××,你们还打啥呀!抓活的还可以回去请功。”他就是这样牺牲的,掩护首长脱离了险境。这时他是机枪班的射手。
关于六师成立的时间,我不大清楚,可有是1936年,最早也超不过1935年。在六师里,跟着师长的有30多人,下边有两个团,七团里朝族多,八团里汉族多。师下边还有副官处,共有10多个人,主要搞后勤工作。粮食和军械都由副官处分配。副官处有个医官,他叫林春秋,团下边没有营,直接是连。警卫连直属师部,实际就是教导队,往各连派干部都从这里边抽,最多时有二百来人,最少是也有一百多人,三个足排,不轻用这个连,师长时常给他们讲话。
二师师长叫曹卡巴眼。这支部队打击敌人打的很厉害。
四师师长是谁,我们不知道。只知道崔贤是四师里的某团团长。四师战斗力很强。另外,还有个毕团长,外号叫毕老疙瘩,他不是四师的就是二师的。这个人是大眼睛,很朴素,有一次他从外面回来,有个警卫员也不认识他,以为他是战士呢,就和他开玩笑的说:“来!你替我蹓蹓马吧!”毕团长说行,结果就替他蹓了一会。后来,这个警卫员听说他是团长,可有些害怕了。毕团长和崔贤的兵力很强。
关于改为方面军的时间问题,我记得是在1939年的秋天。那时,我们对小帮胡匪冒充我们队伍的就进行缴械,好的留下,对大帮胡匪则动员他们进行抗日。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行不通,而是用“拜把子”的办法拉关系,争取他们。
六师的活动地区主要在东满和南满的一部分,如:长白、临江、安图、抚松、和龙、辉南、通化、汪清、桦甸、磐石、濛江等地。特别是长白、临江、抚松、安图、濛江等地活动的就更多一些,这里有些县是靠着鸭绿江的。
在六道沟我们也打过仗。从十二道沟到二十四道沟都打过仗。
四师活动在松花江头,二师活动在集安一带,夏天到鸭绿江边的时候多一些。
1939年敌人来个大“讨伐”,到冬天时,六师就把部队集合起来,夏天就分成小部队进行活动,这样可以灵活的去打击敌人。部队的指战员确实牺牲不少,也出现一些叛徒。在长白县有个姓姜的大儿子就叛变了。
改为方面军以后,编制没有动,人也没有减少,损失了一些,以后又都补上了,还是千余人。
(二)
关于六师越境问题。记得有过两次,第一次越境是在1937年春末的一天晚上。从二十四道沟、戛八山一带,鸭绿江当时水很浅(我们八团没去)。越境以后包围一个日本鬼子的局所,全部消灭了该所的鬼子,得了20条麻袋和黄色炸药。
第二次越境是在1938年,哪月记不清了。地点同前次,都是黑天过去的。是七团、师部过去的,卡了一个小火车站,打了一个日本棚子,在一个山上布置了兵力,我们用石头打击了敌人,得了两挺机枪。这次去没得什么东西,得了一个大金柜,把打不开,以后发现各山头都有日本鬼子在各山头放枪,这时我们就回来了,日本鬼子一直追赶我们到二十四道沟,乱石瞧。我们就打枪回击,吓的他们就爬在石缝里,我们又往下滚石头把他们打的够呛。不然他们始终追我们。我们渡江时大家都是手拉手互相帮助渡过的,在渡过去以后,日本鬼子没有马上发现我们,当地竟是小山包子。师长说:“我们到朝鲜了”,白天就去松树林子里宿营,晚上就急行军,走了140多里路,天将出太阳,没有山了,走到长着杏棵子里又隐藏起来了,这样活动一个多月。师长常开会,拿地图研究地形,原来想找几个伐木工人,都跑掉了,于是就找几个朝鲜人给我们做响导。以后到了一个地方,有一条日本鬼子木场的小火车道,这里交通便利,敌人汽车很多,这天晚上我们还没有发现敌人。第三天晚上就开始攻打日本据点,那里的警察除了朝鲜人就是日本人(即守备队、关东军),我们师部由师长指挥攻击,打死了40多个日本人,其中有工作人员和武装人员,其余都跑了,我们得了几支手枪和一些手榴弹等等。还得了一个半间房子大的仓库,当时没有打开,用斧子劈,用机枪打也没打开。第二天早晨天亮敌人的汽车满道上跑,从各处都往我所在的山上打枪放炮,并开始四下搜山。我们就猫在杏条棵子里,敌人就用刺刀拨开杏树棵子寻找,我们就不碰着不动,相差只有几十米了,结果没有发现我们。那时我们白天不敢活动,因为敌人碉堡严密,每一高地都有碉堡。我们活动了一个多月得些大米和干萝葡条子就回来了,那次把敌人打的够呛。日本的报纸说:“红胡子过朝鲜了”,于是东京又派了很多部队来朝鲜。在那一个月的活动中我们没有损失。在那里活动时如果进了屯子暴露目标就没有人,我们进屋什么也不动,散些传单。但是为了找部队给养,我们有时就包围了屯子,找他的负责人,要些大米,当时情况很紧急,我们宣传他不信,所以我们也有强制的,这时,日本鬼子中知道有金××到朝鲜活动来了。他们在各地公布如果有拿到金××的有赏。那次活动对中朝两国轰动不小,鬼子公安队的头头也被撤换了不少,因为他们没有抓住一个“红胡子”。我们回来以后,开了大会,师长在大会上说:“我们这次过朝鲜去打,胜利了,给日本鬼子很大打击。虽然没有得到多少武器,没歼灭多少敌人,但是影响很大,东京也知道了”。他这样鼓励大家,这说明中国的抗日联军不但在中国能打击日本鬼子,而且还可以去日本鬼子家跟前打他们。
乔邦信回忆:关于六师和中央的联系问题,是1938年七、八月间,我们在行军途中遇到两个人,他们俩个大概是中央派来的通讯员(我当时是师长的警卫员)。原来我们疑为这两个人是“密行团”(特务)的,我们就把他们二人送去师长那里和他谈话。这俩人从身上拿出秘密文件,这时才知道是中央派来的,从苏联边境过来,又通过汪清、珲春、图门一带到这里。他说他们见过朱德、毛泽江,两个人有40多岁,和我们讲了两天两夜,讲了关里的八路军情况,说八路军已来到热河,很快就会和你们会见的,抗日快胜利了。他们还教我们歌子,在他们走前师长又找他们谈的话,吃的饭。他们穿的很破,我们送给他们胶皮水袜子,他们哭了,以后又秘密送军部去了。连他们带的文件也都送军部去了。从那以后,我们的病号等就往苏联派,这是否与他们来有关系不详细了。
关于六师活动情况。师长的命令非常严,命令一下必需马上执行,对敌人行动估计非常准,对行军计划的非常好。如估计我们什么时候行动,敌人什么时候赶来,这样往往我们每当在离开某个地方走出10里路左右时,必听说敌人就去包围了。所以我们行军没有被敌人包围过。比如有时饭都做好还没开饭,听到情况马上就走。师长是地图不离手,每当休息就看。他每到一地就开始计划下一步行动,计划吃饭、出发的时间。
师长很关心下级,我的手被子弹把骨头打碎了,就是他用剃头刀子亲手给我开刀敷药治好的,那时我怕用刀拉痛,他就给我讲“关云长一边剔骨疗毒,一边下棋”的事来,鼓励我,我当时上便所时手都不能提裤子,他就看我上便所,然后帮我结裤腰带,本来行军每到一地,警卫员负有给首长烤鞋袜等责任,可是他反而给我烤鞋袜等,把我感动的哭了,他就说:“不要哭吗!中国朝鲜一样,我们都是打日本。师长也可以给警卫员结裤子烤鞋袜”。那时他有一个毯子,剪成两片,给我一片用。他常和战士一起唱歌,他会唱“骂毛仁寿”。有时为了锻炼警卫员的警惕性,黑天偷偷的把枪拿走,或把手枪匣子的子弹梭子抽出去。他常逗着我们说:“小五子你想家不?你如果想跑的话可要告诉我一声,不要把我的枪带走了”。
乔邦义回忆,战斗事迹。1938年秋收的时候,在临江的板石沟子岗打了一次反包围仗。那次我们和杨靖宇一起被包围了,这次是六、三、四师和独立旅集中的,大概想打县城。敌人也集中了七万多人。那次战斗我们打死敌人很多。我们一点亏没有吃。那次日本鬼子死了几千人,负伤也有几千人。那时敌人的力量是很多的,上有飞机,一去就是三架,飞的很低,左三层右三层的包围了我们,我们的兵力有六师、三师、四师、独立旅(方强旅长)和一个军部。
当时我们正在开会,开了三、四天了,还演了一夜的剧,我当时在大树上放哨。这时内部有叛徒告密通信了,我们也发觉了,作了准备。因为当时我们驻地面积很大,一个师驻地方园五、六里地,敌人也用了几个县的兵力来包围。他们到时,我们已经开完了会。这时就叫四师往东北突围,目的是吸引敌人主力,以便我们主力出去。我们六师、三师、军部、独立旅就在临江的板石沟子岗走了一天。敌人又来板石沟子岗包围我们,这时四师已经出去了。敌人另外又调了一部分兵力想从后面截我们,用簸箕形包围上来。我们突围一天,在板石沟通岗下面宿营,敌人已经发现我们,想一举把我们消灭在沟中。于是我们第二天早晨又继续突围,我们六师为先遣队。三师在后尾、军部和独立旅在中间。六师八团是尖兵,前进到离岗顶三、四百米的斜上岗子时就打响了,敌人就把我们包围在沟里和半山岗中,这时后面也打响了。敌人也越来越密,我们也往岗上冲锋40多次,损失了40多人。冲到岗梁上我们就不冲了,这时敌人又从底下往上冲,上头飞机扔炸弹,机枪手榴弹打的都很激烈,我们也打退了好几次敌人的冲锋。以后双方都不冲了,形成对持。这时敌散发传单,用“铜墙铁罗阵”包围我们两三天。第二天我们又突了一次围没有成功。这时敌人就用一切力量散发反动传单,叫杨靖宇投降,并说:“杨靖宇过来给当通化省长,否则你插翅也逃不了”等等。白天飞机也散传单。这时我们也有个别向日本投降了,并暴露了我们的兵力集中情况。到第二天晚上,召开团干部会,准备分两路突围。我们突围时就专往火堆密集地冲,估计那里敌人是虚张声势,我们还不打枪,都用刺刀拚。于是便攻进了第一个火堆子,又抓了一堆敌人,就叫他给我们带路,告诉了我们敌人的口令(一个班守一个火堆),于是我们就很快的冲出去了,这时敌人还不知道,团长下令加旺火堆,我们一路还抓了不少俘虏。听说我们出去以后,敌人还发动了一次很大的进攻,结果打个空,而且他们自己打死自己不少,我们突出去后就分开了,六师往长白一带,独立旅和军部往北满一带去了。我们抓的俘虏最大的是营级,连级抓了不少。这次前后是两次,第一次敌人没有包围成功。这次战斗是杨靖宇指挥的。以后听说敌人为了装尸,把七个县城的棺材都买光了,还没够用(板石沟子岗离县城约一百多里地左右)。
打辉南县是魏拯民指挥的。他带一个八角帽、穿绸段子,围一条围巾,高个子圆脸盘,口才很好。
1939年春天,我们从密营出来,第一个战斗就是卡道。我们顺着敌人讨伐溜子跟下来了。我们在离和龙木场20里地宿营。我们的目的是想顺一条小沟爬上山去准备打木场子。我们晚间到,第二天早晨敌人讨伐队就上来了,想顺小路赶上我们,但是没有发现我们。因为我们的目的是打木场子,所以也没有打他们,把他们放过去了。七团出去抓来了三个木场的工人是赶爬犁的(跑了两个)当时没有吃的,还抓来一头牛杀吃了。我们询问了这个木场工人关于日本鬼子讨伐队的情况,于是就分配了任务。七团的任务是卡道打通往和龙道上的日本鬼子,包围一个炮台。八团的任务是打一个炮台和主攻局所,我们出发时天好黑了,到山顶上看见了敌人工棚、局所等。师长布置我们为主攻力量,我们连每人披上白布和团部向局所进攻,其余的人进攻另外两个炮台。局所里有四、五十个日本守备队。当时规定我们进攻局所这边不打响,那边进攻炮台也不打响,局所在沟里头。当我们往下进攻时,敌人探照灯照来,我们就爬下,不照了我们就往下跑。和七团约定一起打。这时敌人岗哨始终没发现我们,我们一直出溜到局所窗下,等了四、五分钟,看见了以前跑的那两个木场工人在这里被日本人严刑审问,打的直叫唤。我们就更着急了,这时开火时间也到了,我们就把枪从窗口往里一伸,喊了声“不许动”!其他同志就把门踢开进去了,我们一枪没有打,就把敌人的机枪、步枪、手榴弹等弄到手了。抓了一个日本鬼子,有些空手逃跑了,我们完成了任务。这时我们圈了些老百姓,都是白俄(他们之中很多都是反动的)叫他们每人给我们抗4袋白面。另外两个炮台也打下了、缴了械。我们得一个大仓库,有不少白面、大米、白条肉,我们背出来很多。临走前放火把仓库烧了,不给敌人留下。天快亮时我们就退出来了。这时敌人十八团(十七团)?追上来了,并且又调了七个县的公安大队都是炮手,有三、四百人追了我们四天。我们为急行军,在半路插了不少白面(即藏起来)。在半路一天晚十点烙饼准备一天吃的到第二天将亮,我们在和龙三道沟进行了埋伏,不准打枪要听命令。那天上午日本没有上来,中午也没有动静,快到午后一点时,师部令二人一班轮流睡觉、吃饭。到下午四点传令兵报告“日本来了!”我们看见敌人都背着背包上来了,先头是尖兵排有30多人,当这30多人走出埋伏圈时,后面大部分就接着上来了,等大部分来到我们卡子界里时,师部就下令打起来了,机枪、手榴弹一齐打出,这些鬼子一枪没有放,就跑散了各打地势逃隐,并且依地势开始向我们射击。我们也冲了几次被打回来了。以后敌人端机枪冲上来,被我们一个叫“小锁子”的从后边用刺刀从腹部刺穿夺来机枪。这时我们就一齐往下冲,抓了70多,活的都杀了,共消灭了300多人,解决了战斗。日本鬼子临死时还喊“天皇万岁”。这次我们也死伤30多人。敌人跑了一个尖兵排和后尾的一部分,在搜战场时,迂见敌人半死半活的还拿枪打我们,我们把这些敌人都打死了。这次战斗得六挺“马克辛”机枪和很多步枪、手枪及大量子弹,还得四架电台,因为无人会操纵都砸碎了,还得不少“十四年式”手枪。
七团多为朝鲜族。打局所一般均以八团打,因为日本鬼子抓住朝鲜族就杀掉,抓住中国人还可能放掉。所以敌人和七团就打死仗,因为七团对俘虏也不大讲究。就连我们过去有时恨急了也逮住俘虏背着首长就杀掉。所以敌人就更恨我们了,我们有一个小小锁子,是个很好很勇敢的小孩,参军还没有枪高,以后被他们俘虏给大卸八块了,然后穿心吊起来,非常残忍。就这样更引起我们的愤恨了。
中朝人民是非常团结的,这也反映在部队里面。特别是领导同志,不分中国人还是朝鲜人一样对待。六师绝大多数是朝鲜人,如果领导同志是朝鲜族,那么当中国同志有缺点有错误的时候,往往都是一般教育和原谅过去,但是如果朝鲜族同志有了缺点和错误,就很严格,甚至对一事追根到底(七团是全部朝鲜人,八团是中国人),那时一旦粮食缺少时便互相支援,师部常下来人调查生活情况等,得来牛肉都按人数分配,做饭以连为单位,一连一个司务长,炊事员多为朝鲜族妇女同志。
提起朝鲜女同志做饭真是不容易的。每连只有一人或二人担任炊事工作。每在行军时,他们都背上四、五十个保险盆,司务长背一个大锅和一个帐棚。他们和部队一样行军。有时上山上岗连人带东西滑跌下来。有个女的,是个共产党员,把胳膊都跌断了,而饭盆还没有扔掉。有个炊事员外号叫小丫蛋子,在八团团部做饭,后到师部做饭,只有十七、八岁,他是吃在后边做在前边,宿营时就找水打柴禾,吃饭时剩多多吃,剩少少吃,饭后刷盆洗碗非常勤恳。在宿营时因行军赶上下雨,衣服都淋透了,她就帮助烤衣服烤鞋,而她自己的裙子淋透了,拧一拧就干活。我们每天只睡三个小时的觉,而她们只能睡一个半多小时的觉,有时做饭困的把头发都烧了。“小丫蛋”对伤病员也非常关怀。当时我们都是吃的大包米粒子,小丫蛋就把包米粒一个一个的用石头砸碎了做好,给伤病员吃。
关于军队的政治学习情况,学习都是以连为单位,有文化教育和宣传员讲解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讲关内的八路军、新四军生活战斗情况及军队作风,蒋介石不抵抗出卖中国主权等等,还讲东北三千万同胞热切的等待我们去解放他们和日本帝国主义不但侵略东北,而且还要侵略全中国,我们的任务就是在东北打日本,拉他们的腿,以牵制他们的力量,阻止他们的向关里侵略进军,另外还讲敌人暴行。如在一个地方,敌人以开会为名,架机枪“点名”,然后又把村子烧光了,就以这些实际例子和形势教育大家。
文化学习,主要是学识字,夏天在土地上学,冬天就在雪地上学,有时行军在背包后面写个大字,一天认识一个字。
武器装备及来源。大多数都是从敌人手中缴来的。我参军时,大多用“七九”式,以后换了“三八”大盖和歪把子机枪。1937年以后我们缴来的武器多了,大家就挑好的用,坏的都烧了或插起来了。重武器为重机枪、迫击炮,大部分都放起来了,我们的服装大部分都是缴自敌人的,有扒敌人死倒的衣服。
修械所没听说有多少人,只知师部有一个,以后缴敌人武器多了,也用不着有修械所了,弹药所没听说哪里有。
(三)
几位烈士事迹
乔邦信回忆,1937年4月,我们哥五个一起参加抗联,我大哥、三哥、四哥都牺牲了,只剩我和我二哥。魏拯民是政委兼副司令,我们1938年打辉南是他指挥的。是大个,30多岁,白净子,据说是高级知识分子。以后,有病大家背他爬山。什么时候牺牲的不知道。
1938年8月,团长外号叫钱大包,是山西人,后脑长个大包,是在打辉南时牺牲的。作战非常勇敢,在下午四、五点钟牺牲的,抬出一里多地火葬了。
我四哥是六师警卫班长兼机枪射手(警卫共28人),跟六师长到军部开会回来走到五道阳岔被敌人包围,为掩护师长,我四哥牺牲了。我从1937年至1945年一直跟着六师长,以后跟他到长春。1939年冬到苏联去的,当时我们就是在那里学习了。
乔邦仁是我大哥,会朝鲜话,做地方工作,由于内部出叛徒被敌人包围负重伤被俘在长白县,被敌人用麻袋装上填到冰窟窿里牺牲了。
朴乐全,外号中疤拉,是中队长,1947年因病死在延吉了。曹亚范外号叫曹卡巴眼子,那时顶多30多岁,很瘦,中等个,眼睛不大,小脸,剃光头,经常带战斗帽,打腿绑,一军二师师长。他这个师战斗力很强,伪军都知道他的部队厉害,开会时他的警卫员说,在一次战斗中曾与日本军官进行白刃战,手刃日本军官(在抚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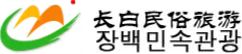

 吉公网安备 22062302660105号
吉公网安备 22062302660105号